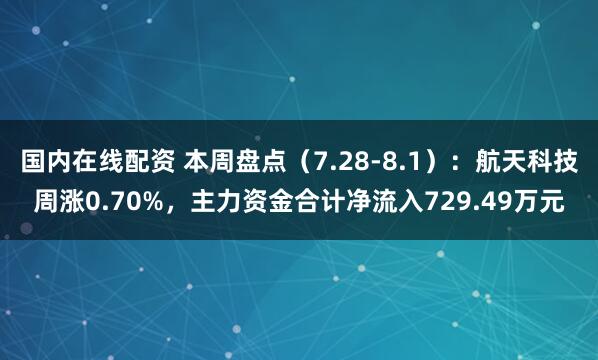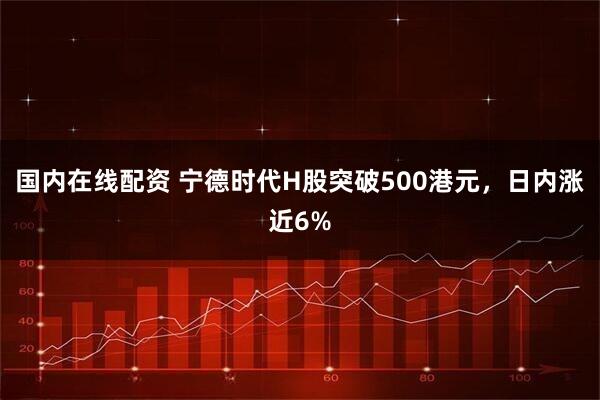看完刚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由建团350年的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瓦格纳第一部树立自己独特“革新乐剧”的歌剧作品《漂泊的荷兰人》,我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脑洞和后现代的剧本改编和导演展现形式,让这部已经诞生了180年的浪漫主义的歌剧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贡献了社交媒体的热议。由弗拉基米尔·尤罗夫斯基担任指挥的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的深情现场伴奏,联手马尔特曼和华莱士领衔出演的荷兰人和森塔完美地诠释的感人肺腑和直冲天灵盖的男中音和女高音,让上海的观众纷纷感叹吃到了“细糠”。但是导演彼得·康维奇尼在21年前的改编,尤其是第二幕的动感单车的展示,又让人忍俊不禁,低声感叹这是我们能看的吗?莫不是邪修了瓦格纳。典型荷兰画派的云的舞台背景和名画“夜巡”这样的服化加持,和部分群演摸鱼,单腿上体重计,永远摇摆的路灯和带有危险品标识的炸药桶这样不普通的道具和动作细节,活灵活现展示了当代观众的跳脱精神现状和超前混搭。
展开剩余77%《漂泊的荷兰人》是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是一部有着瓦格纳浓郁个人经历的重要早期里程碑。歌剧的核心故事源自欧洲流传数百年的“幽灵船”,传说的核心是一位被诅咒的航海者:荷兰船长因亵渎神明,被上帝判处永恒惩罚,终生驾驶幽灵船在海上漂泊,每7年才能靠岸一次,只有找到一位对他绝对忠诚的女子,诅咒才能解除。若女子背叛,诅咒将永远生效。这也正是后来一系列由强尼·德普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加勒比海盗》的原型故事,在电影中,这艘船和它的船长戴维·琼斯,就是《漂泊的荷兰人》神话的直系后裔。值得一提的是《加勒比海盗》电影配曲的作曲汉斯·季默也是德国人,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瓦格纳这部《漂泊的荷兰人》作品的影响,在最新上映的音乐会电影《汉斯·季默和他的朋友们》中,在具有主导性的音乐故事线中,他甚至讲到他如何一夜之间用音乐创造出一个历经风霜,沉重但也带有一些调皮的海盗船长,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两位音乐人在隔空180年间的一种创作呼应。
《漂泊的荷兰人》创作于1839—1841年之间,正是瓦格纳人生中最困顿和漂泊的阶段。他因为欠下巨额债务,被迫与妻子逃亡,计划经海路前往伦敦,再到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巴黎。巨浪滔天和船只飘摇的切身感受,让他对海洋的狂暴与终极的孤独有了极致体验,直接转化为歌剧第一幕中幽灵船与挪威船在风暴中相遇的震撼场景。因为早年创作的《仙女》等作品并无任何关注和成就,他在精神上的孤独感,尤其是对浪漫主义艺术的革新理想与当时欧洲歌剧界以威尔第为代表的意大利歌剧的炫技和商业成功格格不入,让他自我的精神漂泊感与“荷兰人”的永恒诅咒形成镜像:“荷兰人”渴望获得少女无条件忠诚的爱以解除命运的诅咒,瓦格纳则渴望获得观众对自己艺术的共鸣以排解精神上的孤独感。歌剧中女主角森塔对荷兰人献祭生命表达的忠诚,本质是瓦格纳对艺术知音/伯乐的理想投射。
我们无法听到瓦格纳当时创作的心境,但是在汉斯·季默的电影中,我们听到讲述故事的人反复提到寓言故事,那些简单,但是让人思考的故事,带有一种高于现实的命运和高维的预示性。海洋是命运的化身,风暴代表诅咒的狂暴,平静代表短暂的希望和对浪漫想象的投射,用自然的极端对比隐喻人物的悲剧命运。“幽灵船”“永恒的诅咒”“少女殉情救赎”等元素,打破了古典主义的理性与和谐,以非理性的神秘论和少女宿命的悲剧打动观众,成为浪漫主义歌剧的典型范式。它是对“流浪与救赎”这一人类永恒主题的探讨,也是瓦格纳艺术理想的第一次集中爆发。
同时,这部作品还不断地影响着后世的作品,比如小时候大家都看过的《丁丁历险记》。《丁丁历险记》作者埃尔热本人就是一位古典音乐和歌剧爱好者。在他笔下的哈尔卡斯船长就是一位狂热的《漂泊的荷兰人》粉丝。他的许多背景和特色,如与大海搏斗的经历,暴躁但善良的内心等,都与《漂泊的荷兰人》中的荷兰船长有某种精神上的共鸣。当他和丁丁在海上寻找沉船时,他反复地哼唱“荷兰人”的咏叹调“Die Frist ist um”(期限已到)。这首咏叹调完美地映衬了哈尔卡斯当时在茫茫大海上追寻祖先宝藏的复杂心境。就连卡尔库鲁斯教授的管家内斯特的太太,也被塑造成一位世界著名的歌剧女高音。在故事里,她多次演唱剧中森塔的咏叹调,其高亢的嗓音甚至具有“震碎玻璃”的威力。我在看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版的歌剧时,每当森塔的扮演者华莱士一开金嗓,我的脑海中就出现内斯特太太的漫画形象,挥之不去。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版《漂泊的荷兰人》在上海的首次演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除了演出的诚意:百位演出人员,近10吨的舞台装置,高质量的演奏和演出外,也是都市当代人流浪漂泊感的精神共鸣。2025年都市人的漂泊除了精神状态,更多是在生活状态上的。在一个以光速变化的超级大都市里,目标永远在前方,永远有下一个岸要抵达国内在线配资,但抵达后往往发现那只是另一个航行的起点。这种永不停歇的追逐,与荷兰人无法解除的诅咒有异曲同工之处。“荷兰人”的救赎是真爱、森塔。我们的是什么?当森塔点燃了炸药桶,我笑了,不是对于魔改的不解,是对于真爱自体性的觉醒,和投射破灭的认同。我们是荷兰人,也是森塔,每一个都有着对理想伴侣、生活目标的梦幻想法,但是生命本身的脆弱和不可控,有时会把梦想砸个稀巴烂,但是你会发现,生活还在继续,甚至以一种更好的方式。
发布于:上海市富才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